
作者:方麒
嘉庆十二年(1807年),福州怀德坊48号-52号(今道山路新112号-126号)的几座旧宅(林春溥故居资料参考自《福唐林氏林齐翔支系家谱》),迎回了它们的主人——嘉庆丁卯二甲进士、在京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功臣馆纂修、顺天乡试同考官,因母病告假返乡照顾的林春溥。
1809年,母丁忧守制后的林春溥,前往鹭门(厦门)玉屏书院承接主讲一职。在此后的几年中,他请人修葺了怀德坊老宅。1813年间,他请来了善书的舅舅陈登龙为自己的书房(一说为书楼)命名。陈登龙写下四个篆书大字——“竹柏山房”,此斋额后来竟成了林氏居所的代名词。林春溥在这里奉养老父、教养儿孙,也在这里研究史典、著书立说,留下了众多心血著述。
世守儒风的林氏后人们,也以竹柏山房为起点,延续着一门书香风雅。
据林氏后人记载,竹柏山房故居长约39米、宽为38米。因旧48、49、50号临街小店面为他人所有,所以故居呈倒置L型。从街面上看房屋为分隔式,但内部却是座座相通、连为一体,均为二进五间排或二进三间排的坐北朝南建筑。每座均有前后厅、前后天井(空地),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。旧51号为正大门,大厅内悬挂许多钦赐挂匾和荣誉彩匾。52号配有大花厅(接见贵宾用)和被林春溥署名为“竹柏山房”的书楼。旧48、49、50、51号北面和今林则徐纪念馆相邻。

林春溥画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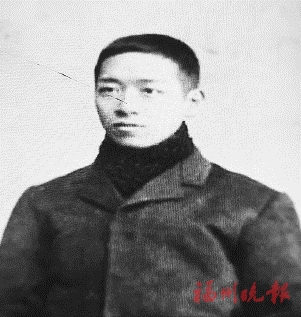
林志钧
一
林春溥(1775-1861),字立源,号鉴塘、讷溪。他是乾隆二十年(1755年)乙亥举人林兆泰的第三个儿子。
林兆泰(1744-1830),字宗期,其人读书甚勤,少时便常“夜读每至三鼓”。林兆泰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恩科福建乡试中举人,与郑光策、郑大坤、龚景沆、许作霖等同年。后来专心教书育人,历主上洋、福清、屏南、厦门玉屏紫阳、南浦各书院讲席,“所至诱掖后进,学者翕然从之”“游其门者因材就范,无不成名”。
林兆泰的育教生涯里,目前可以确切知道的是,他至少培养出了四个进士,其中两个是他的儿子——次子林春溶与三子林春溥,另外是他的两个学生:陈兰畴,清嘉庆元年(1796年)二甲进士,庶吉士,提督学政,1807年掌湖广道监察御史;朱锡谷,清嘉庆六年(1801年)进士,历任四川巴州知州、成都知县、泸州知州,著有《巴州志》等。
被寄予厚望的林春溥,在父亲的教导下,“弱龄即淹贯群经”。后入读鳌峰书院,累试常居榜首。读书之余,林春溥还跟着舅舅陈登龙学习书法、绘画。
林春溥的母亲名唤陈宴。陈宴是福建侯官人,家住文儒坊,其高祖为陈丹赤,曾祖是陈一夔(以难荫授夔州知府),父亲是陈大经。
陈丹赤(1616-1674),字献之,号真亭、津城。他是顺治八年(1651年)的举人,历重庆推官、刑部主事、刑部员外郎、兵部郎中、浙江按察司佥事等职。康熙年间,耿精忠叛乱,陈丹赤不降被害,忠烈殉国。卒赠通政使,谥号“忠毅”,康熙还曾亲书“名垂青史”额以旌其忠。
林春溥的舅舅陈登龙(1742-1815),字寿朋、秋坪。室名水曲云凹、荔竹山房。他是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举人,后署天全州,署里塘同知,官建昌捕盗同知,还曾主讲泉州清源书院。
陈登龙多才多艺,他博涉典籍,能古文、诗词,又善琴棋书画,尤长于山水,善篆书。著有《出塞录》《里塘志略》《蜀水考》《天全闻见记》《读礼余篇》《秋坪诗存》等。其诗书画对林春溥三兄弟都影响颇深。
林春溥没有辜负父亲与舅舅的教导,他比他的二哥、道光十五年(1835年)中进士的林春溶早了三十多年登进士第——嘉庆七年(1802年),林春溥考中二甲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被派习国书(满文)。与他同年进士的还有他的同乡、后来被誉为楹联学开山之祖的梁章钜。
嘉庆十年(1805年),散馆考试,林春溥钦取满汉翻译第一名,获授翰林院编修。后来,林则徐、郭尚先都曾向他学习过满文。此后至嘉庆十三年(1808年)丁母忧离京还乡前,林春溥还担任过功臣馆纂修、顺天乡试同考官。
回乡守制的翌年,林春溥又遭逢丧妻之痛,心中悲怆无奈,转而前往鹭门(厦门),在玉屏书院从教八年。这样直到嘉庆二十二年(1817年),林春溥方还朝供职,先后任国史馆纂修、庶吉士满文教习、顺天会试同考官等。
道光元年(1821年),林春溥得到道光皇帝召见,被“认为可用”,随即被钦点为文渊阁校理,诰授奉政大夫。其前途看来一片光明,并且还有擢升的可能。但当从家书中得知父亲年老大病,林春溥辞官还乡终养老父的决定下得没有丝毫犹疑。
而这一次辞官,是他和仕途的第二次,也是最后一次告别,从此投身教育,成就了无数后进。
二
以道光十年(1830年),也就是林兆泰辞世的这一年为界,此前,林春溥一直待在福州,一边奉养父亲,一边扩修了其父之前在乌山天皇岭的讲学之处——朱文公祠,在此授徒课艺,也潜心学问。父亲病故后,林春溥应邀就教于浦城南浦书院,同时兼主江西鹅湖书院讲席。
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林春溥应福建巡抚魏元烺之聘,接任鳌峰书院山长。直到咸丰二年(1852年)因年迈请辞的十九年时间里,林春溥一直主讲于鳌峰书院。
他以渊博学识,循循善诱,深得书院学生爱戴,“远方之士,多来学”。他也认真负责,面对书院每月繁重的课卷,从不怠慢,而是一一校阅,悉心修改并留下评语,也因此,他常常都要批改到深夜。而看到学生的精彩之作,他也会细心保存下来,“嗣后将之结集付刊,以为后学程式”。有朝廷督学来闽视察鳌峰书院后,对林春溥大加赞赏:“宋学兼能通汉学,经师并可作人师。”
无论是为官、从教,甚或是闲暇之时,林春溥“未尝一日废书”,一直致力于学,尤其在经史研究方面,更是投入,留下了许多著作:《战国纪年》《开辟传疑》《孔子年表》《古史纪年》《榕城要纂》等,著述三十多种,达二百余卷。后来,林春溥将他认为的重要著作收录于《竹柏山房丛书》,据说在其离世时,该丛书已有85万余字。
这些著述钩沉稽古,贯串百家,自然有其价值。梁启超更是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写下如此评价:“林春溥著《竹柏山房十五种》,皆考证古史,其中《战国纪年》《孔孟年表》诸篇最精审。”
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林春溥病逝。他没能等到朝廷在次年举办的琼林之宴——他本也在受邀之列,被准重赴恩荣宴,还被赏加了四品卿衔。
斯人已逝,但其人其神却在著述中永存,也在其培养的后进心中不灭,被后代仰慕者载录常青——同治六年(1867年),诸生呈请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;同治九年(1870年),入祀乡贤祠。光绪九年(1883年)壬午科,有朱氏典试使者,认为林春溥乃闽中钜儒,将其名字写在了乡试录后序,“上于朝”;后得到时任广东提督学政推荐,林春溥“奉旨列国(清)史儒林传”。
三
林春溥育有三子,长子林懋勋,次子林懋烈,三子林懋杰。他将从父亲那儿习得的儒家之风、乐育之怀,毫无保留地教给他的儿孙们。与林春溥很像,他的后代中,人才辈出,他们无意于仕途上的更多进取,而是致力于学问著作、传道受业,比如林春溥长子林懋勋、林春溥曾孙林志钧。
林懋勋(1801-1867),字铭石,号少塘。道光二年(1822年),举乡试第十九名;十六年(1836年)登二甲进士。进士及第后,林懋勋奉旨发往东河学习。临行前,林春溥殷殷嘱咐道:“河工责任綦重,习多奢侈,汝出外任,宜勤习公事,俭约自矢。吾家世守儒风,汝宜识之。”此后,林懋勋还担任过礼部仪制司主事、精膳司主事,又回籍襄办过团练,因功晋秩四品,补员外郎。
但林懋勋生性恬淡,于仕进无意,也像他的父亲一般,将晚年的生活投入于教育——有十余年的时间,他都主讲于兴化府金石书院、省城越山书院,并于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任越山书院山长。此外,还有资料载录其还曾主南浦书院与平度州书院讲席。林懋勋在士林间颇有时誉,“及卒之日,士林惜之,谓经师人师,难复得尔”。
林志钧(1879-1960),字宰平、则平,号北云、唯刚。林懋烈三子林齐翔之子。林志钧少时曾跟着其堂兄林志煜在家中桐荫山馆读书,打下学问基础。二十岁前后,林志钧拜入谢章铤门下学习诗词古文。后来,他曾写有一诗《梅生旧藏谢枚如师八十岁小影题诗见贶赋和谢之》回忆恩师:“卅年重过赌棋庄,更上乌山致用堂。弱冠记逢开讲盛,始衰弥觉受知长。文章寿世徵余集,杖履留真识瓣香。回首师门同一恸,蹉跎谁复问行藏。”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林志钧中举(与沈钧儒同为癸卯科举人)。受时风影响,林志钧未继续举业,他在福州学习日文的东文学堂短暂任过干事,1904年即留学日本学习法政。于1907年归国后的二十余年里,林志钧先后任外务部日本股股员、外务部佥事、司法部参事、司法部民事司司长、司法部部长等职。
政务之外,精于书画、诗文的林志钧也表现出了其文人、学者身份的活跃。他参与宣南画社的活动,与友人一道在京津地区倡导章草,与陈衍、陈宝琛等同光体闽派诗人往来密切,也结识了许多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,比如梁启超、王闿运、林琴南、陈三立、樊增祥、余绍宋等,交谊深厚。
梁启超(1873-1929),字卓如,号任公,又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等。
1912年10月,梁启超结束流亡海外十余年的生涯回到北京,此后,林志钧就开始与其有了往来。1913年,梁启超在北京万牲园发起修禊雅集,林志钧即在受邀之列。此后随着梁启超将重心转移到学术方面,二人的交往更加密切。二人的交游“从政治延及学术,从佛学兼及诗词、书法”,思想契合,尤其在学术方面,林志钧也为梁启超提供了诸多有益创见。
1929年,梁启超辞世,林志钧克尽朋友之道,参与梁启超丧事,并被委托整理编订梁启超的遗著。
林志钧不负嘱托,花费数年时间,整理了约一千四百万字的《饮冰室合集》,分《文集》16册,《专集》24册,合计40册,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。而这部《饮冰室合集》也自此成为梁启超著述最为周备的经典版本。
《福州晚报》(2023年11月9日 A07版 闽海神州)
